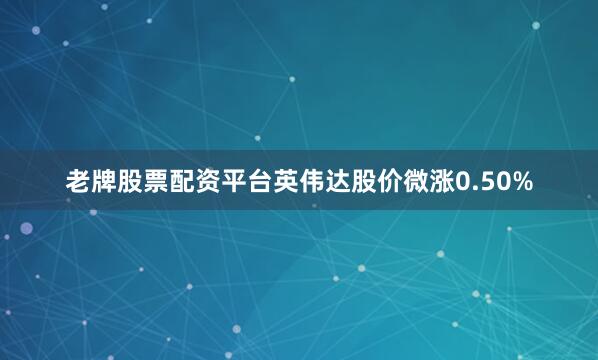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他从地方小官一路冲进权力核心,辅佐仁宗42年,镇边防、主和议、统大军、当宰相,人前是功臣,死后却被列进奸臣传。
问题到底出在哪?从他上朝的第一步开始就埋着雷。
这个黄州小吏,不太听话
那年黄州来了个新司理参军,名叫庞籍。地方小官,按理说该熟规矩、躲是非、混日子。
展开剩余91%可他上任第三天,就把州里三个讼案原判撕了重审,理由写得密密麻麻,拿的是律令里的死条款怼原判官。
结果事情传到知州夏竦耳朵里,本以为是刁民起事,一问才发现是这个年轻参军干的。
夏竦没发火,反而把人叫去当面聊。
两人一来一回,不是客套,是抡典章、比案例,越聊越狠,最后夏竦脱口一句:“你以后能当宰相。”
这是公开场合说的,传出去,有人佩服,也有人咬牙。
庞籍这一脚,算是踩在了别人升迁的脚背上。
从黄州调入京师,庞籍一路顺风,接了开封府兵曹、法曹的活。
这个部门,眼下正收拾一摊子乱账。
谁在挪粮、谁在瞒案、谁在窝藏兵役,往年睁一只眼就过去,庞籍拿着律令一条条过,谁该罚就罚,动真格,结果搞得上下都怕他。
他不怕得罪人,是真的不怕。开封出了一桩官宦之女伤人案,对方是户部侍郎家的亲戚,按惯例私了就好,他一句话不说,直接挂上堂,当场判责、收监、抄家。
朝里有高官放话:“这小子不懂回旋。”他照样照规矩走,不该放的,一个也不放。
这事还没过多久,景祐三年,宫里出了一件更大的事:仁宗宠妃干政。
外朝有奏章说尚美人干预军政,尚未查清。庞籍直接上疏,点名内侍、弹劾尚宫、请求杖责传话太监。宫里一下炸锅。
这奏章进宫那天,御史台门口停满马车,谁都看得出,有人要被弄了。
弹劾宫人,这在宋朝等同于拿头撞铁墙。
事情没压住,第二天早朝,庞籍被外放,广南东路转运使,一句“另有任用”,就把他从京里扔到边陲。
可他没收。刚到任,就向中书门下密呈一份新状:再弹范讽。
范讽是权臣,是“内线”。这份状子再次爆出来,政敌再按他“挟私报复”,朝廷一度要查他是不是疯了。
结果没有查出问题,查出律条都能自洽,没一个是空口说白话。
这是庞籍真正上场的开始——他不是靠站队上位的,他是靠把每一条律令当匕首用出来的,这种人,不好惹,命硬。
延州边墙刚砌完,兵谍就摸上来了
庆历元年,庞籍接任延州知州,这个地方,一半是州,一半是战场。
朝里给他封的头衔叫“沿边安抚使”,意思就是你要盯死西夏动静,不许出岔子。
他到任第一件事,不是开茶宴,也不是见部属,而是让人送来所有城防图和兵力表。
第二件事,拆了三座空寨,重砌五座边墩。
延州边上散着不少叫“望敌台”的高地,他在每个高地下驻扎五十人,分昼夜轮岗,一天一报。
军中怨言爆炸。按旧例,冬月防线松,人人都等着年节休整。
他来了全改,日夜操练、守夜翻班、口粮限发。
军士叫苦,城内绅士更受不了,说他“苛令难行,令人罢极”。他一句回应都没留,只在巡查笔记上写:“人若懈,边若溃。”
一个月不到,西夏动了。夜里传来军报,说有西夏斥候出现在阴山北麓,向西南推进。
庞籍没惊慌,命人连夜传军号、封路、部署反击点,然后静坐一夜,不言不动。
第二天黎明,边军回来,击退敌斥、斩首六人、活捉一名翻译,带回军营。
他亲审,问一句:“你们为何此时来?”那翻译咬牙说:“你们换守太快,情报来不及。”
这一仗没人记名字,但这是庞籍用律令和军纪打出来的“边防口碑”。
延州百姓第一次说:“城里这官,虽严,有用。”
皇祐二年,他上调入京。没进城就接密令:入枢密,监中书。枢密使,是兵权所在,他是那年唯一从边将提拔入京的政务大员。
次年,拜中书门下平章事,兼修国史。
这时候,朝里不少人开始怕他。怕的不仅是他敢说、敢弹,更怕他执法狠。
他定过一个令,军士犯强掠,鞭百,后再犯斩,每个案卷上附三页纸写明案由和律例对照,无一空格。
兵部上书:“此法太重。”他回:“重者,制贼之本。”没有多余解释。
朝中私议,他越当官越没人敢接近,一见他上朝,其他大臣自动绕路走。枢密院门口,每天纸案堆成山,他审的快,批的快,拒的不留情。
那一年,有人第一次把“庞青天”这三个字贴到他门上。不是称赞,而是警示。
西夏声息,边疆风暴
庆历元年,庞籍披甲上阵,从书桌转身走到边寨。延州没给他家宴、没给他准备欢迎牌,他一到城门,只听见寒风呼号、军号四起。
这地方,离京城远,离和平更远。
他第一步干什么?拆三座旧寨,砌五座新楼。
那些据点早就年代久远,风化得厉害,他让工匠连夜拆、连夜建。碎石和木板的声音恰似战鼓,每晚都撞在将士心头。
这动作听着粗暴,但效果见得快——夜间搜敌,旁人都懵了:边将敛兵、巡逻断魂。
他每天巡视,不高兴就敲军中铁鼓,声如山崩。边将私下有怨:日夜操练,口粮限发,人都撑不住。
绅士们在城宴上说他苛,不近人情。他没理,笔记本上直写:“懈者,边溃。”
边兵试图顶撞,一名小将越线言语,他当场下令,军法公开审理。
判决一出:鞭二十,流放边寨半年。
他审案连夜写下十余页案卷,案卷码齐整,每句话没一个空格。
一夜,传来西夏兵影,他没泛情绪,只等黎明。天亮,他起兵,出奇制胜。
杀敌首六,将领俘回审问,那个翻译告密,说:“换人太频,情报无法传。”他说:“小动静,说明我们在边线上做得对。”
这一仗无名,却在百姓耳里算崩地动。
传回京城,朝堂官员清一色双眉紧锁,战略冷眼下,他这手段像铁,一寸不让。
他回京路过殿试门,几个同僚看他眼神像是看着死人。
皇祐三年,他到了枢密院。军政里的大佬们带着酒,先是向他敬酒,又低声念两句:“军纪太甚”。
他点头应付,酒一喝,就把节奏扭回自己那套:提出裁减冗兵、活人用兵新策略。
他说:“世养兵务多而不精,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”
这话有参考价值——据记载,宋冬期军事开支占国家财政六大块中的五分,早成隐患。
他当上宰相那阵,枢密院、三司一起商议时,他又建议:“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各军额定数、再缺补。”
舍得裁人太难,也适度松绑,有人称这是他稳边风暴后的理智一面。这盘棋,下得正在点。
臣子们觉得枢密院门口那份劲,有点像野狼来了。有人贴出“庞青天”,不是称赞,而是提醒彼此:你没命站这里很快。
他从不过场面,志在实质,从边寨铁血,进到朝堂斤斤计较那个“制度”。
庞籍看清宋朝困局,从边到京,他一路踩人行事、不留情面。
权力高悬,家事灭火的最后一役
当他越来越近核心,冲突也越来越剧烈。
皇祐五年,他外甥赵清贶收钱被抓。一年后,御史韩绛上书,说开封吕公绰授意棍毙赵,灭口灭迹。消息砸得朝堂炸开。
他在朝堂上站立,没人敢看他,他,主军主政主法,家里出了案子,这个案子牵涉他名声与拷问。
他站台说:“属我外甥自赃自罚”,绝不承内谋。
这句声音压得上朝气氛哽咽。可过程无力,朝中大佬韩绛反弹劾,这事声势起。
这时他掌权三四年,枢密都多事。很多将领指他太坚持律法,不讲“宽”。
说法狠、防守强,影响士卒和边臣感情。这门庭虽然权势如山,却防着风声。
随后,他被罢相,调往东平。衔落人走出京门,群众围观。有人私下低声说:“赢得旁人恐,他既往的铁腕现在变成“忌惮力度”。”
出京那日,他没回头,扛着衔子,脚步硬朗,目光空洞,像一个被吊起的操盘手。
这人晚年没官职,到东平也没开始写史书修法律。年过七旬,1063年去世,谥号庄敏。
后世史书清楚写他“律令深峭”,“士卒畏服”,“声望逊于边疆时”。
从科举起步、用律法上位,再从边疆成名,到枢密主政,他无疑是北宋中坚力量。
他靠手法精湛、节奏快、冲突密集,干成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:边防稳住、军队整顿、财政算账。
可,人心远比城墙复杂;军纪太严会熄灭士气,好人会被逼退。
掌权久,外甥案爆,就成导火索。那条核弹,是野心的式微,也是律法边缘的边界破裂。
他最后挂“奸臣”帽子,不是因为没做事,而是因为做得太极致,包容少,冲突多,在权斗逻辑里没选边站。
发布于:福建省658金融网配资-正规炒股配资-在线配资门户-10大股票软件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